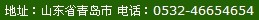|
点击星标收藏我,第一时间看好文◤ 有元一代蒙古人入主中原长达年,河东各地也留下过蒙元时代的诸多遗迹。直至今天,一些地方还保留有不少蒙语地名。 年我写过一篇小文章,说的是临猗县阎家庄乡南王村,当地人呼作“那儿卓naerbfo”。“卓”是“庄”的俗读,“那儿”是蒙古语“淖儿nur”的对音,汉语的意思是“湖泊”。另据方志记载,该村还有一个名字叫“王家胡同”,而这“胡同xutuok”一词也是蒙语“池泊”“水井”的意思。可能由于当时村里建有大池泊积水,所以人们给它起了个蒙古语名字,叫“淖儿庄”,也就是汉语所说的“泊池庄”,口语音转为“那儿卓”。文章曾得著名女真学、蒙古学专家金启孮先生首肯。 就在那个时候,我还注意到万荣县的一个村名,这就是三文乡的“生番村”(又名文村庄)。“生番”是明清以下汉族对少数民族的称呼,如清魏源的《圣武记》:“惟凉山内生番,多不火食。”《清史稿·穆宗记》:“日本兵船抵台湾登岸,与生番寻衅。”前者指彝族同胞,后者指高山族同胞。由于这个原因,我怀疑这里曾有蒙古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居住。但问过几位当地人,都不清楚。 去年在市里搞地名普查,四月底的一天,万荣县地名文化专家解放先生忽然打来电话,说《东文村志》记载,本村一位老教师讲,他看到过村里早年间一块石碑,上面记载说:文村在元代时候村名叫“文也那”,是蒙古语。但不知道这“文也那”是什么意思。还说,村民传说当年村里曾住过蒙古人。这个说法不经意间证实了我先前对“生番”村名的推测。我说:村民的说法有道理,“文村”很可能是个蒙古语地名。又问:当地还有没有其他关于蒙语地名的说法?他回答说,不远处有个“乌苏村”,村里有人说是姓乌的和姓苏的最先住在这里,但本县文化学者陈振民说“乌苏”是蒙古语“水”的意思。不知何者为是。我说,陈先生的说法是对的,“水”在蒙语中呼作us,汉语对音有乌苏、乌素、五素、吾素、勿素等多种写法,还有单译作“素”的。内蒙古有个“毛乌素沙漠”,“毛乌素”蒙语就是“水质不佳”的意思。 但是,“文也那”在蒙古语里究竟是什么涵义,我一时还弄不清楚。当时想到了两个与它读音相近的名词。 一个是奥地利首都叫“维也纳”,与“文也那”读音相似。但那是印欧语系词汇,而蒙古语则属阿尔泰语系,两者对不上铆。另一个是“维那”“都维那”,这是个佛教词语,指寺院里管理僧众事务的一种僧职。古代许多寺庙里碑刻上都有“维那”“都维那”的名字。然而当地村民言之凿凿,是“村名”不是人名,是“文也那”不是“维那”,是蒙古语不是梵语,故这个词语也被我排除了。于是暂时存疑待考。 其实关于“文村”的村名,我在此前是留意过的。年,一位家在文村的朋友要嫁闺女,请我写一篇“之子于归”的文字。当时我就打听过“文村”村名的来历,结果仍不得要领。于是只好“望‘文’生训”,写了几句“十里文村文脉长”之类的话,看来是有点“‘文’不对题”了。但从那时开始,“文村”这个地名已经在我脑子里挂了号。 后来我查阅了有关资料,认定“文也那”这个村名应当和它所处地理环境有关。 文村是个山区乡镇,地处稷王山西麓,海拔较高,境内满是沟壑,属于台塬地带。有东文、西文、南文三个“文村”,俗呼“十里文村”,现在称作“三文乡”。以地理状貌来看,“文也那”有可能是蒙语“山”的对音,也有可能是“高”的意思。经过反复比较,最后我锁定了后者。查阅资料,蒙语“高、高处”拉丁文转写读音为vendur,词头ve是用双字母拼写的一个短元音,-dur是表示方位的位格后缀。vendur汉语对音有文都尔、文得尔、温都尔等不同写法。ven用汉语译作一个音节,即是“文”;译作两个音节(ve、n),即是“文那”;译作三个音节”(v、e、n),即是“文也那”,译写不同,但都是“高”的意思。所以从读音对应来看,这是完全相符的。另据《东文村志》载,古代村里有座大庙,人们呼作“高庙”,庙中还有一通记载元代“重建高庙”的石碑。无独有偶。永济市古代也有一座寺,因建在栲栳台塬上,地势很高,当地人呼作“高寺”,蒙古语则称作“文纳寺”。当地并由此形成了两个“高寺村”,上高寺又名“西文纳”,下高寺又名“东文纳”。这里的“文纳”音义都等同于“文那”(不是僧寺里的“维那”),是ven又一种汉译写法。永济的东文纳、西文纳,也就是万荣所说的东文村、西文村。永济“寺以‘高’名”与万荣“庙以‘高’名”的巧合,进一步证实了“文也那”是蒙古语地名,也说明了蒙语地名在河东存在有一定普遍性。因此,我的结论是:“文”和“文也那”,就是汉语“高”的意思,“文村”意译可以称作“高村”,甚或也可以称作“高庙村”。 时日匆匆,转眼又是一年。 今年四月八号我在外地,解放先生又打电话来提出一个新问题。说是《县志》记载,明朝初年,万泉县老城附近有个“把娄里”,下辖熟里、庙后、上桥头、下桥头、西丁等五个村庄。不知“把娄”两个字是什么意思,是不是也是蒙古语?我说这完全可能。 第一,万泉在元代是个县城,按照元代的官制,县上的达鲁花赤(掌印官)必须由蒙古人担任,故县城一定住有蒙古人。 第二,附近已有“乌苏”“文村”等几个蒙语地名,说明元代人们为当地村落起蒙语名字是有先例的。 但是“把娄”与汉语对应的是哪一个词语呢? 回到运城后,我查阅了相关资料,首先确认“把娄”两个字是表音的,须从音读入手来破解它。但蒙语和汉语分属于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,加上方音和译者口语的个体差异,一个蒙语词往往会有几种甚至十几种汉语译写方式(例如关于“泉”“井”等常用地名字,汉语译法各自都有十八、九种之多)。因此蒙汉语对音不可能是音节声韵的完全对应,重点要看主要音节以及声部。此外,当然还须重视当地的地理及历史人文状况,因为地名往往是一个地方地理状貌以及人文信息的反映。 根据以上原则,经过比较识别,我认为“把娄balou”对应的蒙古语词语应当是“barun西、右”;“把娄里”是“(城)西里”或“(城)右里”的意思。理由是: 第一,地理位置吻合。从地图上看,“把娄里”所辖的五个村子熟里村、庙后、上桥头、下桥头、西丁村,都在万泉县城西边或右侧,故称这一大片村落为“(城)西里”或“(城)右里”名副其实。 第二,读音吻合。蒙古语称西边、右侧为barun。由于汉语中只有边音l,没有颤音r(相当于俄语里的p音),因此人们常将r读作l音,barun汉语对音有的也就译作了“巴伦”甚至“巴隆”“巴楞”等。而“巴伦balun”和“把娄balou”之间不过是一音之转。双方不仅第一个音节ba是相同的,第二个音节的声母l也是相同的。加上人们口语常将n尾音磨损、淡化(如将热气燻xun了呼作xu了,棉mian花呼作mia花),lun(伦)音也就变成了lu(陆)。当地方言又时常将lu与lou混读,将“平陆lu县”呼作“平娄lou县”。这样,在万荣人的口语中,蒙古语barun(口语作balu(n)),就与“balou”几乎没有差别,故将其译作“把娄”是完全合理的。 第三,符合蒙古人命名的习惯。许多蒙语地名都是以方位来命名,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共设有51个旗,其中就有24个有“前后、左右”的方位标识。如乌拉特前旗、乌拉特后旗,鄂托克前旗、鄂托克后旗;阿拉善左旗、阿拉善右旗,土默特左旗、土默特右旗等。蒙古语称南方与前方均为omon,北方与后方均为ar;东边与左边皆称作jun,西边与右边皆称作barun。所以元代蒙古人将万泉城西这五个聚落命名为“把娄barun里”,既可称作“(城)西里”,亦可呼作“(城)右里”。 那么,“把娄里”所辖的“熟里”会不会也是蒙语地名呢?5月30日上午,我去万荣县进行了考察,并访问了解放先生。 据《万荣县志》记载,这个村庄明初写作“熟里”,今天写作“属里”,旧县志上还作“属李”,人们口语则呼作“府里”。一,写法没有一定之规,说明最初写的“熟”字是表音的,不是表意的。二,“熟里”最初见载于县志,而编撰志书的人一般对“属、归、辖、治”之类的地名专用字眼都十分敏感,绝不可能将“归属”义误书作“熟”。因此,“熟里”本义不等于“属里”。“熟”有可能也是蒙语地名。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。 我们知道,万泉话里sh与s不分,u与ou不分,“熟shu”“属shu”和“苏su”“素su”一样,都读作sou。而如前所述,“水”在蒙语中呼作us,汉语对音除有乌苏、乌素、五素、吾素、勿素等各种写法外,还有单译作“素s”的。所以蒙古语“水”,既可以全称呼作“乌苏”“乌素”,也可以单称作“素”或“苏”,用方言对译当然也可以写作“熟sou”“属sou”。另一方面,万泉话“水”的白读音为“府fu”(文读音为粉fei),恰恰又与“熟”字、“属”字的白读音fu相同。这样,蒙汉两种语言关于“水”的音读,竟然巧妙地通过万泉方言的文白异读集中到一个“熟”字上。地名读作sou,是蒙古语“水(素)”的意思;读作fu,则是汉语万泉话“水(府)”的意思。所以,有可能当地人呼作“水(府)”,蒙古人呼作“su(素、苏)”,后来用方言译写蒙语就写成了“熟sou”。可见这个“熟sou里”应当是个记载蒙古语读音的地名,也是“有水的地方”。这里之所以没有再用“乌苏”的“苏”,而选择了“熟”,或许是为了避免“苏姓立村”的误解,强调它是只表音、不表意的外来语。 至于地名“熟里”(水)的命义,当然与周围环境有关。万泉县本来就是以“城临山涧,地多涌泉”而名。熟里位于城西北郊,周边也有涧溪、泉水,附近还有桥头、桥上、涧薛、北涧、南涧、下涧等与水相关的村名。而据解放先生讲,旧时确有一股溪流从孤山流经该村的沟涧。这在水资源匮乏的黄土旱塬上,显得弥足珍贵。人们取其“有水(府fu)”的特点来作村名,用蒙古语呼作“熟(苏、素sou-su)里”也是完全有可能的。 据此,我们初步可以确定的万荣县境内蒙语地名有四处,一个叫“文村”,是“高”的意思;一个叫“把娄里”,是“(城)西”的意思;还有一个“乌苏村”,一个“熟里”,都是“水”的意思。 此外,还有两个村庄因元代驻有蒙古人或色目人而得名。一个是“生番村”,前面已经说过。新修《万荣县志》书作“生蕃村”,释为“盼望草木繁盛,五谷丰登,村富民殷”,亦合“雅驯”的原则。另一个是解放先生提出的“胡村”,因为“胡”也是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的称呼,且该村既无胡姓人家而又与驻过蒙古人的“乌苏村”相毗邻。此说有一定道理。 今天,除“把娄里”已不存在外,其余几个村名都被保留下来。这是地名文化一份珍贵遗存,对研究元代历史和地方文化都是有助益的。 王雪樵赞赏 长按北京中科医院怎么样京城白癜风康复天使
|
当前位置: 上高县 >河东文化万荣县为什么这么多蒙古语地名
时间:2018/7/3来源:本站原创作者:佚名
------分隔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上一篇文章: 今日上高领导到乡镇调研指导工作
- 下一篇文章: 6月12日今日上高
- 热点内容
-
- 没有热点文章
- 推荐文章
-
- 没有推荐文章